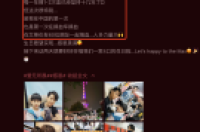摘要 : 清代有“南袁北纪”之称,袁枚和纪昀洵为文坛巨擘,亦皆为文言小说大家。 若立足两人 文言小说集代表作《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以小说地图的视角观之,多有可比对映照之处。 就小说作品的主要地域分布而言,前者以江南区域为中心,叙事呈“自南而北”的趋势; 后者以直隶区域为中心,叙事呈“自北而南”的趋势; 就南北空间景观的重点意象而言,则有市井与庙堂之别; 就物产与民俗地理的南北特色而言,则有南方山林与北地原野之别; 就南北主要人物群像的塑造而言,前者多写江南客商,后者关注北方循吏。 通过以上的比照探讨,还可见出两书不同的写作策略和叙事笔法,即一为性灵大家,由“戏编”而张扬性灵,一为理学名臣,多考据而说理教化。 两位作者虽有强度相若的“地方认同”情感,却有着迥然有别的撰述心态。
文学地图是文学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按照研究者的相关定义,“文学地图是文学世界中空间信息的图形表征或文字描绘”。“文学地图”研究不同于传统的以时间为主要线索的文学史研究,乃是强调对文学作品中空间维度的各类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和评判的研究。具体而言,文学地图包括了作家籍贯地图、作家活动地图、作品描写地图、作品传播接受地图等,而以作品描写地图的研究最为常见。本文讨论的“小说地图”即属于作品描写地图的范畴,其研究旨在通过对特定文本所展现的描写空间进行复现,并与现实存在的地理空间进行比照,从而探寻背后的文学观念及文学规律。
《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称《阅微》)《子不语》与《聊斋志异》作为清代文言小说史上鼎足而三的作品,分别以追踪晋宋志人志怪小说的“笔记体”和继承唐传奇遗韵的“传奇体”,引领文言小说的不同发展路径,掀起清代文言小说的一轮创作高潮。其中《阅微》与《子不语》同为笔记体小说,均以志录妖狐鬼怪等奇闻异事为内容,写作时间相近,时代背景相似,似乎属于同调作品。其实,袁枚与纪昀的小说集,虽同为志怪,但两人的立足点与视野却有较大差异,若以小说地图的视角观之,作品中的地域分布与作者的“籍贯地理”与“活动地理”密切相关,一为南人,且归隐于南,一为北人,长年游宦于北,所见所闻有别,作品之文本风貌和审美理想存在差异,构建地域个性的空间要素亦有明显不同,两书借由小说地图所反映的南北地域个性十分醒目,透过作品地域分布、地理要素呈现、主要人物塑造等空间要素,可以揭示隐含于作家意识深层的心灵图景。
毕萍、刘钊编著《中国并称名人辞典》
一、江南与直隶:小说作品地域分布的南北重心
整理两书中故事涉及的地域空间并加以统计分析,可描画出各自完整的小说地图。结合两书成书时间,本文主要依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疆域政区划分展开分析。
《子不语》与《阅微》故事的地域分布虽然颇为广阔,也有着明显的重点区域,前者多集中于江南(今江、浙、皖、赣)一带,后者则聚焦于直隶(今河北、天津、北京)一带。较于小说涉及的其他零散地区,这些地域在故事的集中性与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它们或为人物籍贯、游历地,或为故事发生地,或为异闻来源地(包括作家听取异闻的场所和讲述异闻的人物来源),出现方式多样,不一而足。由此形成了景观各异、南北映照的小说地图。
两书中的小说地图与作家的籍贯地理与活动地理大致契合,可以发现两位作家的生平经历、地域流动与小说聚焦区域之间关联密切。作为故乡仕宦、隐居游历地的江南之于袁枚,作为故乡的河间、仕宦地的京师之于纪昀,不同地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会触发作家的内心,产生相应的地理情感认知,而作家又将其诉诸笔端,并以审美化的形式予以表达。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一)《子不语》:以江南为中心的作品地理圈以及“自南而北”的叙述趋势
《子不语》中的故事地域分布广泛,东南至福建、台湾,西南至云贵,西北至于西藏、新疆、甘肃。我们将该书小说地图主要分为三部分:江南圈层、岭南游历带、直隶京城圈层。
在《子不语》的小说地图中,以浙江省、江苏省故事数量为最,记录了天台、雁荡、洪泽湖、太湖等自然风景名胜,也有苏州阊门商业区、杭州天竺寺、伍相国祠等人文景观。袁枚从出生求学到仕宦归隐都不离江浙,晚年出游岭南时亦到访过江西、安徽等地,故作家将聚焦江南的生平经历投射于创作,便形成以江浙为主、皖赣为辅的江南小说地图。其次,作家曾两次赴岭南一带,首次广西之行使其写下大量记游诗,沿途的观览听闻也成为小说中故事异闻的素材来源;第二次为暮年出游,足迹遍布东南沿海与岭南一带,书中许多故事恰为其游历时的所闻所见,由此以桂、闽、粤为代表的岭南也是小说地图中一个重要的地理区块。第三为直隶京城圈层,袁枚在21岁时入京应试,分别考取举人进士,并入翰林院深造,这一赴京赶考求学的经历也投射于小说地图,使京城成为小说地图中为数不多且较具典型性的北方地区。
总的来看,江南是全书出现数量最多、频次最高的地理空间,也可以说是作家一生中最重要的地域空间。据统计,全书江南圈层的故事达750余则,在全书1 200余则短篇故事中占比超过半成。此外还有近20余则故事言及“江南”“吴越”却未点明为具体地区,这类宽泛指称也当归入本圈层。它们或为故事发生背景,或为主人公行经游历地,或交代人物与素材来源,或仅作为宽泛地理背景,在叙录异闻时被附带提及,叙事功能明显,本文均纳入统计。其中江浙是构成小说江南圈层最主要的区域,达600余则;皖赣次之,共150余则。可见在江南区域,形成了以江浙为主、皖赣为辅的基本格局。
袁枚著《子不语》
浙江省为270余则,有近20则以“浙、浙中、浙西”等泛指该地。对书中明确提及浙江下辖某地的相关故事进行统计归纳,发现浙江故事的地域分布涉及杭嘉湖道、宁绍台道、金衢严道与温处道。在数量上,主要以杭嘉湖道杭州府(120余则)、宁绍台道绍兴府(40余则)为多。现将浙江故事的地域分布列表1如下:
表1 浙江故事地域分布
这种地域分布的背后是作家出生、求学、游历东南的人生行迹。首先,袁枚祖籍慈溪,为杭州府人,求学成长于仁和县。7岁受业于史玉瓒,12岁得浙江督学王兰生录取,与老师史玉瓒一起进入县学,19岁入杭州敷文书院学习。可知20岁以前,袁枚一直在杭州求学修习,浙江是其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活动区域。故全书浙江故事数量突出,其中尤以杭州府为最,描写到的下属州县也更为具体细致,如作家少时迁居地——仁和县葵巷,小说便有两则故事提及此地且点明为自家旧宅:
吴秉中,居葵巷,故予旧宅邻也。(《吴秉中》)
余幼住葵巷。(《虾蟆教书蚁排阵》)
在浙江故事中,以杭州府故事最多,达120余则,接近半数,且涉及的下辖州县数量更多,以钱塘、仁和为主要地区。
袁枚像
其次,除了出生求学于此,袁枚在暮年应从弟袁树之邀游赴浙闽岭南,“足迹造东南,山水佳处皆遍”。浙南作为其南下的必经之地,沿途观览听闻的内容成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不少就是以台州之天台山(5则)、温州之雁荡山(5则)等自然景观为背景生发故事。可知从出生求学到游历东南,浙江一直是作者的重要活动地。
全书共有330余则故事提及江苏省,比浙江故事数量更多,其中有16则以“江苏”“吴”“吴门”“吴下”等泛指该地区。本文对书中明确提及江苏省下辖道、府、州、县具体地区的相关故事进行统计,发现江苏故事的地域涉及范围比浙江故事更为广泛和具体,包括江宁道、淮扬海道、淮徐道、常镇通海道与苏松太道。在数量上,主要以江宁道江宁府(51则)、淮扬海道扬州府(42则)、常镇通海道常州府(60则)、镇江府(31则)、苏松太道苏州府(77则)为多。现将江苏故事的地域分布列表2如下:
表2 江苏故事地域分布
姚鼐著《袁随园君墓志铭》
这种地域分布也与作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首先,袁枚在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于乾隆七年(1742)外调江苏,先后于溧水、江宁、江浦、沭阳为宦七年。袁枚在父亲去世后即乾隆十四年辞官归隐,在江宁购置、改造随园,暮年在随园与大量文士诗酒酬唱,“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又曾应沭阳人士吕峄亭之邀赴沭阳作客,终于嘉庆二年,葬于南京百步坡。从仕宦到归隐到辞世,江苏是袁枚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地域空间,在江南圈层乃至整个小说地图中地位最突出。
江南圈层的故事分布在数量与集中度上以江浙两省为中心向外拓展,辐射了安徽与江西的部分地区。小说中也有将皖赣两地归入江南的文字记载,如《良猪》中称的“江南宿州濉溪口”位于凤阳府,隶属安徽省;《南昌士人》中称的“江南南昌县”位于南昌府,隶属江西省。这与本文对于“江南”的设定有一定出入,大致处于“中江南”区域的边缘地带。
袁枚在21岁时入京应试,落举后客居京城友人家中,一边为某达官做家教,一边钻研自己极为鄙薄的八股时文,终于乾隆三年中举,第二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深造。对应这段自南而北的应试赶考经历,小说集中也多有类似题材。据统计,在京城故事中有14则明确提及人物由江南至都城赶考会试的活动路线,列表3如下:
表3 赶考会试活动路线
从江南出发,朝向京师,形成了“自南向北”的行旅路线,可见仍有不少像袁枚那样的江南士人由南至北入京会试、投供,开始了他们的京城生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袁枚以江南为本位的叙述视野中,这些故事只是江南生活的延伸和补充。
袁枚手迹
(二)《阅微》:以直隶为中心的作品地理圈以及“自北而南”的叙事趋势
梳理《阅微》中的地域书写可知,作品书写主要集中于以直隶(今京津冀)为主的北方地理圈。全书空间地域广阔,涉及26个行政区划:东至福建、台湾,南至云贵,北至黑吉辽,西至新疆,而以直隶清河道河间府、直隶顺天府以及新疆迪化府乌鲁木齐的笔记数量最多。其中直隶清河道河间府、天津府与直隶顺天府均位于北方,与《子不语》中的江南地理圈形成南北呼应的格局。
依据不同地理空间在小说集中的出现频次、比例,笔者将小说中涉及的地理空间分为四大圈层和一条地理带:分别为河间圈层(300余则)、顺天京城圈层(近200则)、新疆乌鲁木齐圈层(100余则)、鲁苏浙闽游历地理带(200余则)、零散空间(200余则)。由此可见,全书涉及地理空间广泛,由北至南,从中原到西域均有涉猎,为我们呈现一幅广袤且完整的小说版图,这也正是纪昀一生游历的空间轨迹。
纪昀著《阅微草堂笔记》
在地理版图上,如果说《子不语》侧重于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那么《阅微》则偏重于以“直隶”为中心的北方。在《阅微》中,直隶清河道河间府与直隶顺天府的相关笔记数量最多,这与纪昀出生成长以及长年仕宦生活于此的经历密不可分。两地同属直隶地区,故直隶是全书出现数量最多、频次最高的地理空间,即今河北、天津、北京地区。据统计相关笔记高达500余则,在1 100余则笔记中近乎半数。而尽管同属直隶,两大圈层在与作家渊源以及空间元素上均有明显差别。同时,由于顺天府所领二十四县虽在直隶总督辖区内,但府尹和总督不存在隶属关系,北京城垣之内,直隶总督无权过问。故本文将直隶与顺天并列讨论。
在顺天府的近200则笔记中,京师笔记数量最多,超过半数,再加上其地处天子脚下的都城地理位置,本文将以“京都皇城”统括该地理空间;顺天府之外的直隶笔记中,以清河道河间府数量最多,再加上其作为纪昀故乡的地理定位,故本文以“河北乡间”代指除顺天府之外的直隶地区。
“河北乡间”圈层的地域分布涉及清河道(下辖三府、四直隶州)、天津道(主要以沧州为代表的天津府)、大顺广道(主要以邢台、邯郸为代表的广平府)、热河道(主要以滦阳为代表的承德府)、通永道(主要为永平府)。在数量上,主要以清河道河间府河间县、献县、交河县为最多,天津道天津府沧州、天津县为次多。此外有部分未明确提及地名,但出现“先祖”“余乡”“里”等指向性表达的笔记,以及部分具体地名难以考据,但联系上下文可推断发生于该地区的,均归入这一圈层。
纪昀像
“京都皇城”圈层的地域分布涉及24个州、县,主要以北京城为主,笔记分布以北京城区为核心向外泛化。京师之外的州县则以房山县和文安县数量最多。此外在乾隆朝为宦期间,纪昀除了短暂出任过福建提督学政外,其余几十年仕宦生涯均在礼部、兵部、都察院度过,故有大量未明确提及地名,但出现“尚书府”“御史宅”“直庐”等带有皇城特质的空间意象,这些地理空间亦皆归入京师地区。
除以上较为集中的几大圈层外,《阅微》小说地图还呈现出一条始于山东、由北至南的跨区域地理带,这一地理带贯通南北,横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四省,可与纪昀行旅南北的行迹一一对位;且在数量上呈现由北至南依次递减的趋势,可窥见作者与该地理带不同地区之间渊源的深浅、情感的亲疏。首先,山东笔记数量最多,其内容乃是源于纪昀姻亲卢见曾,卢是山东德州人,姻带关系加深了纪昀与山东的渊源,而从姻亲处听闻的异闻传说也成为小说撰述的重要素材。其次,纪昀曾于乾隆二十七年五月短暂出任福建提督学政,督学闽中的经历使福建成为这条地理带中突出的空间节点。而江浙作为南下福建的必经之路,在行旅过程中作者自然耳闻目睹不少异闻传说,为小说创作述录提供素材。此外,该地理带的形成或还与纪昀伴驾乾隆南巡的经历有关。据载,乾隆六次南巡基本都途经江宁府、苏州府、杭州府、扬州府,纪昀曾在乾隆二十七年的第三次与乾隆四十五年的第五次南巡中伴驾跟随,这一经历亦可与本条地理带相互映照。
总体而言,两书在故事分布地域上各具特色,在版图上形成南北映照的格局。相关作品数量反映了袁枚与纪昀的生平与游历足迹,展示出两位作者于空间层面留下的精神印记。袁枚和纪昀分别基于南北文学大家的视角,将个人生平经历所带来的地域意识诉诸笔端,从而展开带有地域属性的自然风貌与人文风情的特色画卷。
清徐扬绘 《乾隆南巡图》第六卷《驻跸姑苏》局部
二、市井与庙堂:南北景观的重点空间意象
在《子不语》里频繁出现江南的酒楼茶馆,真实展现了江南一带繁华富庶、重视娱乐的人文风情。江南的餐饮、娱乐、旅馆业至明清极盛,市民宴饮成风,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以及文士大夫,各阶层、各色人等均出入于大小酒楼茶馆、瓦舍勾栏之间,或在酒楼茶馆聚会宴饮,或在瓦舍勾栏观剧听戏。此外,明清时期的江南作为商品贸易中心,人流往来繁复,往来其间的各色人等需要在旅店驿站打尖歇脚,由此促生了旅馆驿站行业的兴盛。这里的楼馆旅店亦名噪一时,如《子不语》中便有一京城旅店,虽位于北方却以“江南客寓”自号以吸引顾客(《江南客寓》),由此可见江南旅馆业的盛名。酒楼茶馆、勾栏妓院、赌场旅店这些在江南流行的市井空间意象成为小说中大量异闻的发生背景,同时与歌姬舞者、妓女伶人等人物形象,与观剧听戏等民间人文活动相互生发,共同构建小说地图的江南特质,呈现江南商业发达、经济富庶的地域风貌以及民间追求娱乐消闲的人文风情。
酒楼茶肆与旅店驿站是体现江南餐饮娱乐业兴盛的典型代表。尤其是茶肆,明清时从上流社会到市民阶层,饮茶之风极为兴盛。在《子不语》中,茶肆、茶亭常作为故事发生、情节推进的重要空间背景。比如《镜山寺僧》一篇写钱塘王孝廉之父曾在某茶肆中与镜山寺某僧共饮茶,后僧人转世为其儿子的故事;还有《屃赑精》中的无锡华生被屃赑精诱惑,一疥道人见其妖气过重,便将其邀入茶肆,授以道符为其驱怪;再如《缢鬼畏魄字》一则,写濑江有二士相友善,一日暮雨,甲在某茶亭避宿时遇到乙亡妻魂魄的故事。有时茶肆作为空间背景意在交代人物生平,如《全姑》中的美貌女子全姑生于砀山茶肆;有时茶肆成为家境富足的代名词,如《僵尸拒贼》中的杭州贩鱼人成功娶得鬼妻,其子“积廿余年,取媳生孙,家亦小康,开茶肆”。以开茶肆指代贩鱼人子孙的生活步入正轨,走向殷实富裕。
故宫屃赑
与此相类的还有酒肆饭馆、旅店驿站等空间意象,本地或外地来此经商贸易的各色人等在这里用餐借宿、打尖歇脚,由此产生了种种故事。如《符离楚客》一篇,有楚客贸易山东,在徐州至符离的途中“见道旁酒肆灯火方盛。入饮,即假宿焉”。在借宿当晚看见众多军士在酒店豪饮酒食,醒来后发现酒肆已经消失不见,问人方知此处原为旧时战场,自己投宿的当为鬼店。还有《一目五先生》写浙中钱某宿旅店中,“群客皆寐,己独未眠,灯忽缩小,见五鬼排跳而至”。再如《神秤》中的武进县户房书吏张玉奇路过苏州横林,宿旅店中,竟梦见金甲人与青面獠牙者用神秤判定其生平功过。《叶老脱》一篇则写叶老脱投宿维扬旅店时发生的异事,其嫌客房嘈杂故投宿某偏室,竟遇一长舌女鬼与无头鬼在此间作祟。再如《道士留符》中的常州吴某,从京师回乡途中正是在酒肆中遇一风采绝异的道士,后二人交好,道士赠吴某道符为其驱鬼驱灾,这里酒肆成为二人相识、吴某获符的契机。此外还有《吴生手软》中的苏州吴生,在投宿沛县旅店时遇到女鬼欲与之结为夫妻;《葛道人以风洗手》中的杭州葛道人,在投宿酒店时碰到一仙人为其指点访仙之道;《曹能始记前生》则写曹能始先生在暮宿仙霞岭旅店时,碰到自己前世之妻的异事。惯常模式是:某人在江南酒馆驿站借宿因而遭遇鬼怪或神异之事,酒肆旅店在小说中往往附着于这类志怪情节而出现。
而在《阅微》所呈现的北方小说地图中,京师圈层与河北圈层形成一城一乡、彼此对峙的格局,其突出的地理景观与空间意象展现了都城与乡村迥然有别的风貌。在呈现“京都皇城”与“河北乡间”两类小说图景的同时,熔铸了作家个人对仕宦地与故乡的不同情感心态,其中,又以“京都皇城”的建筑景观更具代表性。
在京师小说地图中,作家选取了“都察院”“理藩院”等朝廷官府空间以及“校尉营”“安南营”等军营,突出了其作为行政、军事中心的地域特质。同时长年在京为宦的经历也让纪昀十分熟悉京师的官场,廷府内阁一类空间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很高。
光绪年月“行在都察院”空白公文封
其中多有谈及内阁者,如《滦阳消夏录四》有一则写纪昀自己在直庐(即旧时侍臣值宿之地)时听闻内阁学士图时泉讲述转世轮回的异事;还有《滦阳消夏录五》一则,写自己与张真人共同参加朝廷祭礼,将入朝时张某发现朝珠遗落,便向纪昀借朝珠的故事;《滦阳消夏录二》与《槐西杂志一》则都曾记录在都察院库房中发现巨蟒的异事;《滦阳续录二》一则笔记记录了翰林院正堂关于“不启中门,云启则掌院不利”的忌讳;再如《姑妄听之二》一篇,写兵部侍郎景某在翰林院任职,值班期间偶遇鬼魅讨论文词诗赋的故事。作品集中这类以都察院、翰林院等为空间背景的故事还有许多,有时“朝廷”在小说中并非具体空间意象,而是作为开展派遣使节、设立律条政策、封赏臣子等活动的官方系统的统称,以此表明故事发生的政治情境。
除朝廷之外,还有如理藩院、都察院、六部等各种行政机构,它们作为叙事背景之外,更多以交代人物生平的形式出现,在某行政机构仕宦的某官在某地告知纪昀某异闻,是这类笔记故事的典型叙事模式。如理藩院尚书留公、都察院左都御史舒穆噜、太常寺卿史松涛、礼部尚书陈公、户部尚书柘林等等,包括纪昀自己任兵部尚书时亲身听闻了大量奇闻异事。
董诰(号柘林)像
皇家书阁类文化空间在京师小说地图中也频繁出现。京师作为文化重心,主导官方学术的发展,纪昀作为内阁大学士,担任《四库全书》总纂官,曾先后多次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校勘编修《四库全书》,《滦阳消夏录》便诞生于此时期。《滦阳消夏录一序》有载:
乾隆己酉夏,以编排秘籍,于役滦阳。时校理久竟,特督视官吏题签庋架而已。
清冷枚绘《避暑山庄图》
故小说不少京师故事以皇家书阁类空间意象作为叙事背景。如《槐西杂志二》一篇,写纪昀自己在馆阁校勘《四库全书》时发现世无传本的《李芳树刺血诗》,便托书馆馆吏抄录一份,由于时间过长导致抄本遗失,待自己到滦阳避暑山庄供职,清点旧籍时又重新见到该诗抄本,纪昀在文中借贞魂怨魄之说解释其失而复得的遭遇,这里的馆阁与避暑山庄成为该诗抄本辗转流离的关键空间节点。再如《槐西杂志一》有一则写纪昀与堂侄虞惇一起在文渊阁校勘书籍期间,听堂侄诉说老家异事;《槐西杂志二》一则写自己到避暑山庄校勘皇室典籍,泛舟至文津阁所见的美景;《滦阳续录一》一则写在避暑山庄直庐时与都察院副都御使胡太初、学士恒兰台讨论人能见鬼的异事,等等。总之,这些故事多由作者所处的文化空间生发,带有呈现京师皇家空间形态的地理标记。
此外,小说中还有不少皇家空间意象,比如南新仓(皇家粮仓)、圆明园、西苑、南苑、畅春苑、清秘堂等,它们以独特的皇家属性,成为构建京师小说地图的标识性元素,也反映了纪昀个人身处高位、常伴圣驾的不凡政治阅历。
故宫文渊阁牌匾
三、南方山泽与北地原野:物产与民俗地理的南北特色
除了地标式景观,特产风物也是小说中彰显地域特性的重要空间要素,“南袁北纪”分别从不同的地域视角记录了南北各异的特产名物,呈现了各具特色的地域风貌。
江浙一带历来是富庶繁沃的鱼米之乡,这里水网密布、气候湿润、土壤肥沃,地形多丘陵平原,且有太湖、西湖、东钱湖、鄱阳湖、洪泽湖等众多湖泊,为该地人民种植棉花稻米、养蚕晒盐提供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故江南一带历来是棉布、蚕丝与粮米的重要产地。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依靠大运河和自身优越的水陆交通环境,一跃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这里商品销路广泛,人流往来繁复。
从稻米茶叶到蚕丝布匹,这类物产在小说的江南圈层中出现频率较高,且多与商贩市肆等相关联,是江南商贾文化在文本空间中的体现。据统计,全书与茶相关,包括茶具、茶肆等衍生元素的故事共有50余则,而其中的《阿龙》《叶生妻》《屃赑精》《瘟鬼》《羞疾》《李百年》《镜山寺僧》《诸廷槐》等24则故事就属于江南区域。再如,棉布作为商品,往往附着于布商、布行等元素出现。这些布商或出身江南,或抱布往来江南贸易,如《冷秋江》中“抱布为业”的镇江程某,《项王显灵》中“贩布芜湖”的无锡张宏九者,《恶鬼吓诈不遂》中的江西布客张四,《鬼宝塔》中“贩布营生”的杭人邱老,《僵尸抱韦驮》中“贩布为生”的宿州李九,《医妒》中赴常州贸易的陕西布客,《借棺为车》中有在阊门开布行的绍兴张元公,等等,此时棉布与布商、布行等元素一起,建构起小说中独特的商业空间。
清徐扬绘《姑苏繁华图》局部
在《子不语》中,这些江南物产的呈现多置于市井空间的背景中,带有地域特色的物产空间场景的高密度出现,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袁枚的写作立场:他着意于放低视角,将眼光集中在江南市民阶层,尽可能以世俗化的角度审视和呈现当地市井细民的生活百态。
在《阅微》北方小说地图的两大圈层中,纪昀对“河北乡间”特产风物的描写更为典型,空间特质及作家蕴含其间的地域情感心态更为显豁。纪昀在多则笔记中提到了沧州酒与沧州枣,它们作为作者家乡河北沧州的特产,突出了小说中河北圈层的乡野地域特质。
沧州酒,阮亭先生谓之麻姑酒,然土人实无此称。著名已久……盖舟行来往,皆沽于岸上肆中。(《滦阳续录五》)
余乡产枣,北以车运供京师,南随漕舶以贩鬻于诸省,土人多以为恒业。枣未熟时,最畏雾。雾浥之则瘠而皱,存皮与核矣。每雾初起,或于上风积柴草焚之,烟浓而雾散;或排鸟铳迎击,其散更速。盖阳气盛则阴霾消也。(《槐西杂志三》)
崔庄多枣,动辄成林,俗谓之枣行。(《槐西杂志三》)
束城李某,以贩枣往来于邻县。(《滦阳消夏录三》)
纪昀在小说中借故乡风物,绘制了家乡枣树成林、河水清澈的自然地图,呈现了北方乡人酿酒贩枣、怡然自适的乡野图景。其中对沧酒佳酿的描述尤其值得关注,作家不惜笔墨详细介绍了酿酒、藏酒、品酒的标准流程,运用大量举例、对比、衬托的手法来说明沧州酒的珍贵和独特,此类细笔在作者这部崇尚简澹、惜墨如金的小说集中,是颇为少见的。这些故土风物的描绘在呈现北地乡野地域特质的同时,也熔铸了个人忆恋故土的真挚情思。
沧州纪晓岚文化园
沧州名人植物园里的纪昀塑像
如果说物产代表的是不同区域的物质层面,那么民俗信仰则体现精神文化的特征。两书都属于典型的志怪作品集,在类型上多与传统志怪小说存在趋同性。但共性之外,某些精怪物种和民俗信仰存在着南北有异的属性。
《子不语》在传统狐精形象之外,塑造了许多基于南方地理特征与民俗信仰的精怪形象,形象种类丰富多样,典型如以山魈、五通神等为主的精怪系列。山魈形象来源于《山海经·海内经》。其文曰:“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国语·鲁语》载:“夔一足,越人谓之山臊。”《子不语》中有多则故事谈及这一产生于南方山中的精怪,比如《山魈怕桑刀》一则对其习性喜恶进行详细介绍:
常山璩紫庭贡士,有书塾在东门外山中,时有山魈出没其间,土人习见,亦不为怪,呼为“独脚鬼”。皆反踵而行,其来必有风云。其怪最怕桑刀,以老桑削成刀,斫之即死。悬桑刀于门,亦避去。山魈爱听歌,有张某馆衢州山中,每夜山魈踯躅而来,强嬲唱曲。
《山海经》
再就是由山魈演化而来的五通神。宋人洪迈《夷坚丁志·江南木客》对其有记载: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二浙江东曰“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独脚五通”,名虽不同,其实则一。考之传记,所谓木石之怪夔魍魉及山是也。李善注《东京赋》云:“野仲游光,兄弟八人,常在人间作怪害。”皆是物云。变幻妖惑,大抵与北方狐魅相似。
五通以前文所提山魈类的奇异生物为原型,且在不同时期和地区有不同说法,但无论浙东闽中,出现地点均位于“大江以南”,可知南方多山林崖壁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其提供较好的生存环境,五通由此成为与“北方狐魅”系列相对应的南方精怪形象。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亦称:“南有五通,犹北之有狐也。”由此可知,明清时期的五通神成为南方民间独特的神灵信仰,与北方的狐仙信仰相对。
洪迈著《夷坚志》
相比而言,《阅微》则呈现了一系列以北方原野为主的精怪形象与典型物种。他们的集中分布范围与形象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北方地区的自然生态与人文民俗。
如常见于旱灾虫灾笔记的飞蝗,多出现于干旱少雨的北方平原,再如对狐狸、黄鼠狼、巨蟒等的记载,则多出现于北方的草原与半沙漠的地带。这些动物精怪的故事不仅反映了当地的自然生态状况,也显示了北方“四大门”信仰在民间的广泛流行。“四大门”又称“四大家”,指的是“狐黄白常”四大仙,他们分别以狐狸、黄鼠狼、刺猬(或白兔)、蛇为原型,逐步演化为能够护佑百姓的神灵,成为民间崇拜信仰的图腾灵物。这四种动物在北方民间极为常见。它们长期与人类为邻,多以墓地坟穴、废墟等隐秘场所为栖居地,且行踪神秘,狐鼬之机警狡诈、蛇之噬人凶残,都给人们带来一种神秘感甚至是畏惧感。
王守栋著《古州城市井风貌与民间文化》
《阅微》中谈及“四大门”中的三种,即狐、黄鼠狼、蛇,构成了小说以北方山林为主的精怪生物系列,其中又以“狐”的记载最多。在我国灵物崇拜体系中,狐狸名列四仙之首,唐代以来人们多事狐神,建造狐仙庙供奉狐神之风颇盛,故民间有“无狐媚不成村”之说。纪昀在书中追溯了民间狐仙信仰与历代文献中的狐精故事:
三代以上无可考。《史记·陈涉世家》称篝火作狐鸣曰:“大楚兴,陈胜王。”必当时已有是怪,是以托之。吴均《西京杂记》称广川王发栾书冢,击伤冢中狐,后梦见老翁报冤。是幻化人形,见于汉代。张鷟《朝野佥载》称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当时谚曰:“无狐魅,不成村。”是至唐代乃最多。《太平广记》载狐事十二卷,唐代居十之九,是可以证矣。(《如是我闻四》)
纪昀在《阅微》中多处直言某地“多狐”,归纳了狐精集中出现的地域:
京师一宅近空圃,圃故多狐。(《滦阳消夏录二》)
夜或闻翻动书册,摩弄器玩声,知京师多狐,弗怪也。(《滦阳消夏录四》)
海丰(山东无棣县)有僧寺,素多狐,时时掷瓦石嬲人。(《滦阳消夏录五》)
忽悟北地多狐女,或借通情愫,亦未可知。(《槐西杂志四》)
在小说其他狐精故事中,作家虽没有直言某地“多狐”特质,但归纳狐精集中分布的地域,不难发现其与北方小说地图颇有重合,河北圈层与京师圈层是小说中狐精形象出现的主要区域。
《太平广记》
在特质塑造上,这类集中北方的狐精形象各异。而其中博学懂礼、理性睿智者,洞察人间世情冷暖、官场百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滦阳消夏录一》中的河北献县某狐为当地县令指点迷津,劝其为百姓申雪冤狱:“明公为民父母,但当论其冤不冤,不当问其允不允。”虽为妖媚之流,其睿智正直更甚于人。在纪昀笔下,狐虽为异类,但却与人相似,有善恶良莠之分。《如是我闻四》中作者借沧州狐友之口,发表了自己对人狐之别的态度:“我辈之中,好丑不一,亦如人类之内,良莠不齐。人不讳人之恶,狐何必讳狐之恶乎?”认为人间与狐界之“人情物理,大抵不殊”。由此,作家借这类狐精故事影射人间百态,这些狐精妖媚常与人居,举手投足与人类无异,却又带有灵狐的神异色彩。“鬼狐形象出自作者对人的神化,它们作为一种精神幻体活跃着”。这正寄寓了作家以神道设教,劝诫世人的创作主旨。
桂馥书“阅微草堂”
北京阅微草堂旧址
四、江南客商与北方循吏:南北人物群像塑造的偏好及其地域性格
《子不语》中的江南客商形象颇为典型。南方发达的商品经济造就了小说中大量的商贾小贩,且江南素为鱼米之乡,尤多米客、绢布商人等,这些商人多出身江南或专赴江南进行往来贸易,如《鞭尸》中贸易江西的桐城张、徐二友;《陕西茶客》中贩茶江南的陕西茶客;《骗术巧报》中买货淮海间的常州华客;《僵尸抱韦驮》中赴霍山贩布的宿州李九;《项王显灵》中赶赴芜湖贩布的无锡张宏九……江淮贸易的商人形象众多,不一而足。小说通过塑造这一圈层中形形色色的商贾形象,生动展示了江南经济发达、商品丰饶、贸易繁盛的地域特色。
从人物形象特质来看,江南客商之聪慧与狡黠并举,其中既有灵巧善思、善于挖掘商机的聪慧商人,也有为人良善的情义商人,更有不少奸猾谲诈、钻营取巧的奸诈之徒。聪慧者如《照海镜》中具有商业头脑、慧眼识宝的塘西客商,多加十千文钱从农民手中购得照海镜,并赴崇明卖之,最终得银一千七百两;还有《吞舟鱼》中的盐商在出海时遇吞舟鱼怪,急中生智以盐包投之,最终鱼口获生。有情义者,如《地仙遭劫》一篇,写杭州叶商造花园时发现一位修仙道人,虽为富商却为人良善,不以此牟利,反而对道人照顾有加,“商故富豪,喜行善事,蒸人参汤灌之”,“商意是炼形之地仙功行未满者,将依旧为之覆藏”。再如《借棺为车》中,在苏州阊门开布行的绍兴张元公,信守对伙计孙某许下的诺言,“亲送君归,三四千里,我不辞劳”,情义由是可见。再如《屈丐者》中,苏州枫桥一乞丐路见不平,对欠债者倾囊相助,各米商接济了义举后一贫如洗的乞丐:“所有日收米样,俱着赏给屈丐,免其朝夕沿门求乞之苦。”还有《骗术巧报》中的常州华客,赴淮海贸易,路过丹阳时见“岸上客负行囊,呼搭船甚急”,便大动恻隐之心,“怜之,命停船相待”,并不顾船夫怕客为劫匪的忧虑,“固命之迎客入”。
同时,在江南宽松的文化政治环境中,狡猾谲诈的奸商亦颇为多见。如《屈丐者》中在苏州枫桥镇私自放债、高利盘剥的奸商曹某;《谢铜头》中贩铜为业的镇江谢某,私自销熔古董铜佛,并私铸制钱为事;再如《米元章显圣》中安徽芜湖一位擅长作画且专学米芾的奸商鲍某,“烘染纸作旧色”以欺世取财,“南北古董家购者甚多,因之致富”;再如《狗熊写字》一篇写江苏虎丘一位心狠手辣的乞丐,生剥狗熊皮套在人身上,逼其作字吟诗,以招摇行骗的故事,“一钱许看”,“大书唐诗一首,酬以一百钱”。凡此种种,钻营谲诈在江南已成一时之风习。
与《子不语》中多写江南客商不同,《阅微》中的典型人物群体则是各级官员和地方名士。河间与京城作为纪昀的故乡与常年旅居之地,他或念兹在兹,回望追忆,或游历其中,观察审视。在其笔下,发生于其故乡河间与仕宦地京城的官吏故事集中表达了作者的诸多人生感受和体悟,因而更具代表性。
在官吏形象上,纪昀更着意于塑造品行端正的良吏清官形象,这类形象大都集中于作家故乡河间。这些官员或刚直不阿、正气凛然,如《滦阳消夏录四》中的献县捕吏史某“为人不拘小节,而落落有直气,视龌龊者蔑如也”;或坚持操守、自洁自爱,如《槐西杂志三》中“自是不敢枉法取钱,恒举以戒其曹偶”的献县刑房吏王瑾;或鞠躬尽瘁、忧虑民生,如《滦阳消夏录一》中“颇爱民,亦不取钱”的知州平原董思任;或明察秋毫、断案如神,如《如是我闻一》中“精明果决,又判断如流”的南皮令居公鋐……这些形象体现了纪昀心目中良吏好官的品行标准和职业素养。
袁枚书法联
与河间良吏相对,全书的恶吏更多集中于京城。小说借一系列官商勾结、官府虐奴、昏官颠倒黑白、草菅人命的故事,表达了对当时官场腐败的反思和对清明政治的向往。
在作者的家乡河间,更有一批刚正博学、恪守礼法的儒士,“孤高特立,一介不取,有古狷者风”(《槐西杂志一》)。他们或刚正不阿、品行高洁,或求实尚笃、博闻强识,或长于书画、精于义理,展现了直隶之崇尚古道、学风醇厚的地域文化特质。如《滦阳消夏录一》中,有“博雅工诗”的景州李孝廉;《滦阳消夏录二》中有善讲程朱之学的肃宁塾师;《滦阳消夏录三》中“好讲古制”的沧州刘羽冲;《如是我闻一》中“纯厚朴拙,不坠家风,信道学甚笃”的景州申学坤;《如是我闻三》中“襟怀夷旷,有晋人风”的沧州刘太史;《槐西杂志一》中“衣必缊袍,食必粗粝”的景州申谦居;《姑妄听之一》中“经术湛深,而行谊方正,粹然古君子”的河间王仲颖,等等,甚至人物涉及范围不局限于人界,连故乡的狐仙鬼怪都深谙程朱理学和释道宗义。如《滦阳消夏录五》中专赴寺庙听经的景城野狐、《姑妄听之四》中有才情堪比李清照的景州乩仙等等,足见此地尊儒之风是何等的醇正,尚学之风是何等的浓郁!
纪昀书法联
五、“南袁北纪”的叙事策略及其“地方认同”之文化心态
《子不语》《阅微》与《聊斋志异》在清代文言小说史上鼎足而三,其中《子不语》与《阅微》同为笔记体,共同冲击着《聊斋志异》以传奇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自此,两种不同风格的文言短篇之作,有如双峰对峙,两水分流,自成流派,各极其盛”。二者在体例与艺术风格上多有共通:篇幅短小精悍,体例上均追踪晋宋志怪;结构上不离笔记小说传统叙事模式,基本按时间顺序交代前因后果;语言风格上均承六朝古风遗韵,简短而不失韵味。但“南袁北纪”从不同的审美意识与文化心理出发,采取了不同的叙事策略与笔法。
张俊、沈治钧著《清代小说简史》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小序中,纪昀明确表达了对唐宋以降“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的鄙弃,在《姑妄听之序》中表示反对作者一切带有主观色彩的“怀挟恩怨、颠倒是非”之语,强调作者不能以自身主观意愿任意歪曲事实,故全书在广罗异闻中均以征实态度记之。对于小说地图中的各大空间要素,纪昀以学者姿态一一考证,从传闻来源到历史事实,从方言到特产名物、社会民俗、精怪信仰都予以认真辨析。
在“言必有据”的观念之下,《阅微》在写作中突出了说理的特色。有研究者称:“纪昀写鬼神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宣泄他匡扶世风的良苦用心,因此,他笔下鬼神之形象不是很丰富,而作者以神道设教的用心异常鲜明。其明显标志就是作者的议论随处可见。”全书传述故事过程中有明显议论化倾向,每则故事都存在夹叙夹议的叙事范式,大多由一个叙述者(“言”者)讲述,而辅以一个或若干个议论者(“曰”者)评说,构成全书“言”“曰”结合、夹叙夹议、主从相伴的文本结构。这些议论或开篇明义,或夹杂于故事中间,或作为结尾升华主题,议论说理方式开放灵活,但都紧紧围绕教化劝惩的主旨。较于叙述者所“言”的故事本身,作家更注重议论者所“曰”的评论,所言故事中相互勾连、敷衍出异闻传说的各大空间要素(人物、精怪、空间意象等),服务于说理议论的主体,以达到劝善惩恶、警戒世人的目的。
如果说纪昀的写作策略是由考据而说理教化,那么,袁枚则是由“戏编”而张扬性灵。他在《子不语》序言中直言全书为“广采游心骇耳之事”且以“戏编”为创作方法,由此形成全书自由灵活、随心所欲的笔法风格。
王正兵著《含笑看泰华 请各立一峰:袁枚〈子不语〉研究》
全书述录异闻传说皆随性而至,对史实经典、地理方位自然随性处置,不似纪昀那样多加考据深究。袁枚在《答赵味辛》中自言:“拙刻《新齐谐》,妄言妄听,一时游戏,故不录作者姓名,无暇校勘,谰言误字,不一而足,乞示知以便改正。”在具体叙述方面,小说对各大空间元素的灵活书写主要体现在地名方位上,很少对某城名称或史实追根溯源,“某村”“某城”“某处”等宽泛性的指称极为多见。如《梦中破案》中称:“曹州南城十数里处旧有凉亭……遣二人至某村。”《斧断狐尾》一文有“闻某处有狐仙迷人”。《猪道人即郑鄤》一文有“三十年后,某村有一清贵官无辜而受极刑者……某村翰林郑鄤素行端方”。《真龙图变假龙图》中称“某村有王监生者,奸佃户之妻”。这些以“某地”“某村”“某城”作为背景的故事不胜枚举。故全书并不拘泥于地理方位之真假正误,空间大都作为故事发生背景或为了交代人物来历,仅为推进情节、完成叙事而设置。
袁枚“戏编”之法体现了作家质疑六经、鄙薄考据的学术思想。首先在对六经的态度上,他竭力淡化经典的神圣性与权威性,以此消解汉学考订之意义。其《子才子歌示庄念农》一诗自言:“六经虽读不全信,勘断姬孔追微茫。”其次在揭露汉学之弊上,其《与程蕺园书》一文直言古文式微肇于三误:“一误于南宋之理学,再误于前明之时文,再误于本朝之考据。”他提倡个体创作的自主性,认为过度关注考订、摭拾考据会削弱创作者的才思性灵,《随园随笔》序曰:“考订数日,觉笔下无灵气,有所著作,惟捃摭是务,无能运深湛之思。本朝考据尤盛,判别同异,诸儒麻起,余敢披腻颜帢,逐康成车后哉?以故自谢不敏,知难而退者久矣。”
袁枚著《小仓山房文集》
全书更显灵动的手法还表现为对程朱理学的反拨。其《答金项门》一文自言:“仆生性不喜佛,不喜仙,兼不喜理学。”他对理学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反对理学之专制与禁欲。故《子不语》全书着意放低视角,真实展现江南市井的民风百态,其内容为“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文辞上则通俗浅易,多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这些故事虽然也暗寓褒贬,但作家能以更加客观多元的立场进行审视而不进行直接的道德评判。与《聊斋》相类,袁枚笔下的鬼神同样“眉目言笑,宛若平人”。空间要素中的人物与妖媚,其“人性”“妖性”无论优劣雅俗、美丑善恶,作者一律等距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不加主观评判而将评判权交还于读者,故内容更加生动具体、鲜明形象,呈现了一个充满“情”“智”“俗”“恶”的南方市井空间,更接近于人性本真。
相比于叙事策略,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袁枚、纪昀两位小说家撰述背后的文化心态。作家对所描写地域的选择、对地理要素的设置与处理,不仅是真实地理图景在小说地图上的反映,更揭示了作家意识深层的心灵图景。小说地图不局限于地方空间意象、人文民俗、特产风物的展现,更隐晦标注了小说中叙事主体的文化站位,以及这一站位与地域文化、个人情感、思想认同的多边互动关系。显然,两人都有着明显的“地方认同”情感。在人文地理学者看来,地方感应包括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两个维度。不同个体的地方依恋强度不同,有学者将地方依恋感从浅到深依次命名为熟悉感(familiarity)、归属感(belonging)、认同感(identity)、依赖感(dependence)与根深蒂固感(rootedness),其中,熟悉感是最表面的,而根深蒂固感则是最深层次的。
袁枚对江南的地方认同感贯穿了他整个文学创作,无论是诗文还是小说,江南在袁枚笔下都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地理空间。出生、求学、为宦于此,让他有充足的时间机会对其间的种种社会百态、世态人情予以充分审视;辞官归隐后于南京购置的随园恰处南北交通要冲,是众多文人骚客、达官贵人汇聚之地,又为他搜集创作故事提供了绝佳素材来源;晚年游历四方,充满奇山异水和诗情画意的江南又成为其大量优秀风景诗的描摹对象,承载了袁枚对自然景致的热爱和归隐自适的人生追求。因此,江南之于袁枚是一个熟稔而自在的地域空间。
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
同时,崇尚性灵巧思、充满市民精神与叛逆意识的江南市井又是袁枚理想社会的投射。基于质疑六经和标榜性灵的思想观念,他着意在江南市井塑造了一系列正面人物形象,其中多有不为传统礼俗所容的底层人物,从妓女伶人之流到同性恋者,从商贾小贩到行乞之辈,不一而足。这类江南布衣多机智聪慧,敢于抗衡酷吏士绅和张扬欲望,其背后是袁枚对南方巧智多情之风尚的肯定。
纪昀之“立足于北”的文化心态则带有更复杂的双重性,其中包含了双重的抑扬。首先是对于京师的抑扬,一方面,纪昀在小说中流露出强烈的“京师情结”,这鲜明体现在京师叙事上,故事叙述往往强调某某为京师某某人,或某人曾到京师有某事,以此建构京师故事的典型叙事模式。尽管作家对京师怀有深厚的情感,长期的历练与观察却让他更深刻地看到了京师之恶。小说呈现了一系列官商勾结、奸商行骗、娼妓淫纵等乱象,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悲惨生活,深刻揭露繁盛京都下涌动着的人性人情之恶。
第二重的抑扬在于抑京师而扬河间,通过“河间叙事”来对迷乱京师进行全面反拨。作者故乡河间是全书正面形象出现频率最高的地理空间,而河间素为尊礼守节之地,其好古勤学、敦实守礼之地域风尚渊源有自。阮元《纪文达公遗集序》:“河间献县在汉为献王封国。史称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被服儒术,六艺具举,对三雍、献雅乐、答诏策,文约指明,学者宗之。后二千余年而公生其地,起家甲科,历跻清要。”纪昀《日华书院碑记》:“献县,于河间为大邑,土地沃衍,而人多敦本重农。故其民无甚富亦无甚贫,皆力足以自给。又风气质朴,小民多谨愿畏法,富贵之家尤不敢逾尺寸。”故在小说集中,纪昀塑造了数量众多的节妇孝子、儒士廉吏等正面典型,大力渲染故乡淳朴良善、尊儒尚学的风气。故乡在纪昀的认知中几乎就是良善守礼、质朴淳厚、敦本重农的代名词。
《纪晓岚文集》
综合上述,尽管两位作者所采用的叙事策略有着明显的差别,一人立足于南,一人立足于北的文化站位也完全不同,但是在对于生养之地、主要居留之地的眷恋和感念却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殊途同归,这种情感专注、持续而强烈。这正是我们超越了小说地图的地理意义,在探求小说的精神地图时能够强烈感受到的。
在中国文学审美中,对于南北地域的不同审美情感及表现方式一直被反复比较,南北问题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地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这样概括南北文学特质:“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后来的研究者有进一步的阐发,刘士林在《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中指出了中国传统话语存在两大谱系:“其一是作为中国话语中心的北方伦理谱系,其二则是以中国话语边缘形态存在的江南审美叙事。尽管由于中国文化、人种、地域、个体等差异,有时会出现所谓的‘南人北相’或‘北人南相’的倒错,但用‘北方伦理’和‘江南审美’这个二元叙事来编制一份中国历史文化地图,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本文关于“南袁北纪”的探讨无疑为此提供了经典案例以及鲜活演绎的不同样本。
刘士林编著《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
概言之,清代两位足以并肩的文学大家,著述宏富,文心独运,一南一北,彼此映照,相互激发,堪为奇观。这里的“南北”不仅是作者所处的地理方位,更是一种具有明显统摄性的叙述视角和文化站位。我们相信,本文关于“南袁北纪”研究所传递的重要信息在于,小说地图视角的引入,南北地域比较的路径选择,对于小说史乃至文学史研究具有较为广远的借鉴启示意义,不仅可以为作家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视野,提供新的阐释框架,探索新的学术路径,同时还将为中国文学地理研究提供更具特色、更富想象力的学术案例。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作者: 葛永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黄心笛,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