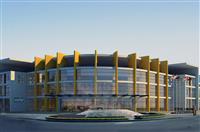马克思是一个穷困潦倒、只能靠朋友接济维持生计的清苦文人吗?
很久以来,「伟大导师马克思穷困潦倒」的叙事深入人心。
许多人脑海里都浮现过这样一个场景:一位穷苦的德意志知识分子,带着一家老小在寒冷凄苦的伦敦贫民窟里,靠有钱的朋友接济苟延残喘,在廉价纸张上用鹅毛笔奋笔疾书。
这个场景极具代表性,可以看作当代小市民对19世纪幻想的典范。
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三个女儿(1864年5月)
马克思真的处在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底层吗?恩格斯对他的接济是地位较高者的施舍吗?
俾斯麦的校友
关于马克思的社会地位,有两个地位需要弄清楚:
一、在19世纪的社会金字塔里,马克思究竟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这个位置意味着什么?
二、基于马克思的身份和地位,他和恩格斯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要弄清楚这两个问题,首先要了解19世纪的社会金字塔,因为一个人的身份,首先取决于他所处的时代。
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1848年革命爆发的时候整30岁。
不妨比较1848年欧洲历史舞台上的其他巨星:法国的社会王子路易-拿破仑那一年40岁;普鲁士的霰弹王子威廉51岁;刺刀反革命俾斯麦33岁;奥地利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18岁。
革命者中,职业革命家米哈伊尔·巴枯宁34岁,萨克森王国歌剧院的指挥瓦格纳先生35岁,瓦格纳的同事、负责舞台布景的戈特弗里德·森帕尔那年45岁。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群人中间,霰弹王子(也就是未来的威廉一世皇帝)无疑是太老了,而瓦格纳、俾斯麦、巴枯宁、马克思和28岁的恩格斯,则均属同一代人,他们都是1848年那一代人的代表。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社会地位的起点。
威廉一世皇帝比奥匈帝国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他爸的岁数还大,但是继位却比弗朗茨·约瑟夫还晚,他这个人一如他在历史上留给我们的印象一样是一个老人
另外,马克思出生的时候,维也纳最后议定书尚未签署,德意志邦联议会则已于1816年召开。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将在复辟时期度过,对德意志来说,这是梅特涅时期,也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二元制的时期。
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的人们在精神上渴望高歌猛进,但由于政治发展裹足不前,大家也就只能在一些出版审查官无法理解的领域里高歌猛进了。
此外,马克思来自普鲁士王国所属的莱茵省,位于德意志的最西端,历来是法国军事或者文化入侵德意志的必经之路。
所以,莱茵地区的人先是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后来又受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影响,虽然根据1815年维也纳合约被划归普鲁士王国,但是从文化到社会结构,莱茵地区都和农业王国普鲁士格格不入。
莱茵省在普鲁士王国的位置(红色部分)
马克思的出身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他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
在德意志西部,对犹太人的歧视政策是被进军德意志的法国人废除的,法国大革命本身也废除了对犹太人的歧视政策。所以,拿破仑时代的另一个犹太少年海因里希·海涅,一生都无法忘记骑在父亲背上观看拿破仑骑马入城的场面。
因此,作为德意志犹太人,马克思的父亲没有从事传统的工商业,反而选择了做律师,在拿破仑战争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此外,他还皈依了基督教。
在复辟时期,一个犹太人作出这样的职业和信仰选择,说明他正打算为自己的政治生涯铺平道路。
画家大卫·李维·埃尔坎于1836年时为马克思做的石版画肖像
综合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马克思的社会形象:他属于1848年的德意志市民阶级。
当时的市民阶级,跟21世纪的市民阶级毫无可比性,因为1840年代前工业化的柏林还只有30多万人口,当时市民阶级实际上并不比贵族多出多少,与今天毫无特权阶级色彩的市民阶级大不相同,不太会被地位下滑的焦虑所折磨。
在工业凋敝的德意志,市民阶级实际上是特权阶层,其上层更是平民和贵族的交汇点。他们如果成为军官、法官或者行政官员,最终结果就是受封为贵族,与贵族阶级通婚更是寻常事。
马克思的父亲皈依基督教,事实上已经迈开了受封贵族的第一步。卡尔·马克思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与一位官僚贵族家庭的女儿结婚,也完全符合他作为上层市民的身份。
马克思的妻子燕妮的画像
马克思的早年生涯,也是沿着这条社会地位升级的必由之路前进的。
他被父亲送进波恩大学学法律,成为了俾斯麦和日后威廉二世皇帝的校友,过的是典型复辟时期大学生的生活,主要精力用来打架、决斗顺便学习,最后也和俾斯麦一样,没能在波恩大学拿到文凭。
波恩大学
复辟时期的大学生也是一个充满使命感的阶层,由于各国君主无限期地搁置了宪法和统一的许诺,所以这些青年学生便通过大学生团体、遍及德意志的大学生联合会联合了起来。
这一时期,德意志学生的体操运动、火炬游行、民族节日聚会都成了德意志的统一之声。
而且,这些大学生在毕业以后,也没有放松彼此之间的联系。公开发行的协会期刊,以及大学生组织的通信和小团体,把这些社会地位不断向上流动的人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
一个1850年代大学生运动里的风云人物,即使是在成为了大臣的校友面前,对方在私人场合也还是会毕恭毕敬。比如一位大学期间决斗失去一只手的德意志小邦外交官,就因此而在各邦外交部畅通无阻,被学弟们奉若神明。
1861年的马克思(43岁)
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认为,德意志人追求统一的基础就是男子气概,而最能体现男子气概的就是战争,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就要用决斗代替;对于法国人决斗使用的佩剑或者火枪,德国大学生也持唾弃态度,而是以马刀互搏。
马克思、俾斯麦等人也都是决斗的行家,虽然两人均全须全尾,但大学时代都是出生入死的人物。
了解过以上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设想,一个思想上不叛逆、循规蹈矩的卡尔·马克思,会度过怎样的一生。
他的父亲已经是基督徒了,而且当时的德意志人把犹太人看作是德意志人的一部分,把意第绪语看作是德语的方言;马克思本人是波恩大学的学生,如果拿到法律文凭,便可在法院实习得到普鲁士公务员考试资格,再通过毫无技术含量的考试进入普鲁士政府。
因为没什么钱,马克思肯定进不了外交部(普鲁士外交官需要财产性收入证明)。作为官僚贵族的女婿,他比较可能的道路是进入行政管理工作,再步步升迁至省长或者议员,不过考虑到他不是贵族,哪怕思想足够保守,1863年也还是当不上大臣。
最后,在漫长的俾斯麦时代里,保守版马克思可能会是一个不太得志的普鲁士公务员,但仍有可能敕封贵族,毕竟他有一个好岳父。
这样的一个循规蹈矩的马克思,大概会以冯·马克思的名字被历史遗忘。
当然,真实历史中的马克思没有选择这样的人生。我们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问题:在他和恩格斯的友谊里,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流亡者卡尔·马克思
以21世纪的标准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贫富差距悬殊,尤其是伦敦时期,前者好像完全是一个仰仗后者生活的清客。
但是,这样理解他们的关系是很有问题的。
19世纪是一个讲究身份地位的时代,马克思虽然穷,但他的社会地位并不低。
作为1848年革命的风云人物、德意志大学运动里的名人,马克思之所以会陷入贫困,是因为他不愿意俯就他出自的那个阶层,因而处于流亡海外的状态。
马克思如果愿意跟他的朋友们和解,回到德国去老老实实的教书,弄一个大学教授的教席、甚至当选议员,混成另一个马克斯·韦伯,也并非天方夜谭。
20岁出头的恩格斯
相比之下,恩格斯虽然有钱,但社会地位并不高,他只是一个工厂主的儿子,从出身上就比马克思低了一点,属于市民阶级里的中层。恩格斯的父亲也没有供他上大学,因此他没有踏进德意志精英阶层,不属于那个封闭的小团体。
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两人的身份并不因为财富的差距而显得悬殊,他们的关系是对等的。
这种情况在19世纪屡见不鲜,尤其是巴黎和伦敦这两个全世界流亡者和冒险家聚集的大都市。
1855年的巴黎
在「19世纪的首都」巴黎,往自己家门上贴奇奇怪怪的招牌,说自己要为了全人类而工作,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和冒险家都聚集在这里,如匈牙利民族主义者、茜茜公主的绯闻男友安德拉希伯爵,1848年以后便在巴黎给小报撰稿、当包打听过活,结果1867年就成为了帝国的外交大臣。
俄国的冒险家巴枯宁,法国的暴动爱好者布朗基,整天用德语骂德国、用法语骂法国的毒舌诗人海涅,气死亲爹后跑到巴黎风流快活的英国王子阿尔伯特(也就是未来的爱德华七世),都聚集在巴黎。
法国报纸漫画,描绘了英王爱德华七世在巴黎的快乐生活
在他们头上,还有一位眼下正高踞宝座的顶级流亡者,那就是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他在瑞士、意大利度过了青年时代,在伦敦靠女士接济才能维持体面生活,四十岁那年作为政坛黑马当选共和国总统,然后发动政变成为帝国皇帝。
对流亡者来说,这就是咸鱼翻身的楷模和样本。
拿破仑三世回巴黎
伦敦的流亡者也是如此,俄国流亡者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夫妇在伦敦同居七年,三人总计生下五个孩子,这个奇妙的大家庭每年给富二代作家屠格涅夫写信请求打钱,后者也会回信解释自己手紧或者「没收到信」。
流亡意味着一个人脱离了自己的祖国,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和背景,但是他们的「地位」并不因此而改变,只是暂时身处困境而已。
虽然除了安德拉希伯爵之外,真正咸鱼翻身的例子凤毛麟角,但是流亡者身上的这种可能性,还是让他们的朋友和敌人都承认他们的地位。
安德拉希伯爵
同样的,如果流亡者当中有个把阔佬,其他人吃他的喝他的也属理所当然。
比如拉斐尔前派的诗人兼画家罗塞蒂兄弟,父亲就是一位有钱的希腊流亡者,在伦敦拥有体面的住宅和体面的生活。
结果,他们的家当然也不可能只属于自己,其他运气不好的希腊流亡者不但吃在他家喝在他家,而且还要找他爸爸要钱养家。在流亡者中间,这种事是理所当然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以另一种视角去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伟大友谊。
1875年的马克思(57岁)
他们都是流亡者,互相帮助是应该的,马克思就算不认识恩格斯,也能从别人那里拿到钱;而在那个时代,身份地位的观念即使在革命者中间都起作用,恩格斯要跟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和冒险家打交道,马克思的威望也能成为重要的支持。
因此,把当代市民阶层的认知简单粗暴地套用到十九世纪的欧洲,并不能认清马克思生前的社会地位。反过来,这种套用也许倒可以用来理解当代人的焦虑。
作者:高林
来源:《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
转载平台:大象公会
近期热文
性:激情、冲突与圆融
陈嘉映:人是自私的吗?
女人越独立,爱情越自由
崇洋媚外的张文宏为什么要反对中国粥?
萨特对话波伏娃:通过思考死亡,去学会如何活着
好文不是搜索得来的,而是不期而遇